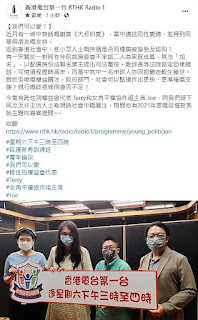節目重溫: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young_politician/episode/758104
Youtube 頻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yThCYrTR0
本集簡介: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日前率團前往北京,參加黨慶。香港代表團成員吳秋北曾表示,過往的黨慶香港參與程度不高,這次上京可見證中共在過往一百年帶領中國走向繁榮,因此是次參與黨慶意義重大。然而在港人看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卻似乎難以參與其中。
七月一日同時是香港回歸的日子。對中國而言,香港「人心回歸」是完全統一的里程碑。然而在建黨百年之際,政治上港人無法參與其中,經濟似乎難以分一杯羹,文化方面又擔心國安法而自我審查。在重重關卡下,香港人如何貢獻國家呢?邁臻研究所總監宋立功博士認為本港施政將會越趨強硬,但香港難以真正地融入中國的問題,又是否能靠即將推行的國民教育甚至國安法加以改善?
中國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中也曾提及港人民心未歸的問題,然而港人普遍無感甚至因中共的強硬態度而心生反感,中港關係的未來又何去何從?特首多次提及「迎新制」,要好好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等規劃為香港帶來的新機遇,又是否為港人所接受?港人所要求的,是否和共產黨所給予的一致?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會因此而提升還是產生反效果?
中國積極發展,然而社會卻開始流行「躺平主義」。共產黨試圖把中國打造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但現實狀況,卻令新一代對生活感到無力,若有人認為躺平即是正義,這會否成為中國發展的阻力?中港兩地新一代的發展,會否成為建黨百年最大的挑戰唔?
有請本集嘉賓,邁臻研究所總監宋立功博士和我們一談中共建黨百年的挑戰。
延伸閱讀:
李泠(2021年7月7日)。〈劉兆佳:中共不在香港公開活動的承諾已不合時宜〉。《觀察者網》,取自:https://www.guancha.cn/liuzhaojia/2021_07_07_597278_s.shtml
觀察者網:這百年來,中共在香港進行了不少活動,党成立初期即在香港發展黨組織、國共內戰時期廣東省委遷往香港等,“六七事件”前香港可謂中國左翼運動的發揚和庇護地。那時中共和親共的左派在香港社會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劉兆佳:香港一直為各方政治勢力提供一個地方,甚至成為庇護所。不只是中國共產黨利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資源獲取和外宣工作,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的革命者或反政府分子,也將香港作為他們行動的基地之一。
但是這些政治活動,其實都是在英國人的眼皮底下進行的。英國人對這些活動非常戒懼、警惕,所以對這些活動,他們採取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防範甚至是控制。如果你從中國歷史角度來看,英國人最怕的是在香港出現民族主義意識、反“殖民地”運動、挑戰“殖民地”政府的行動,以及香港部分勢力與內地的政治勢力密切聯繫,對“殖民地”的管治造成威脅。
所以1967年之前,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活動的能量實際上是比較有限的,因為始終受到在港國民黨勢力的挑戰、英國人的約束及香港的反共分子的阻撓。
當然,可以說中共從1921年成立之後的確在香港有活動,特別是涉及到工會的罷工活動。抗戰期間也在香港組織過一些抗日活動,主要是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
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更多是利用香港支持內地與國民黨的鬥爭,包括運送物資、中共人員來港尋求庇護,甚至讓一些支持中共的民主黨派人士可以在香港得到庇護及照顧。
到了1949年建國之後,在中西方冷戰期間,中共及支持中共的工會、商會和其他民間組織的活動受到英國人的監視和打擊,活動空間更加有限。實際上,中共在香港的勢力或者親共人士、支持新中國的在香港的力量,某種程度上是邊緣化地存在。
考慮到香港社會的歷史背景,有一大批香港人是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的——建國前、建國後有很多人是為了逃避內地的政治鬥爭、政治運動,1962年左右為逃避內地的饑荒而來到香港;當然,有一部分人是為了尋找個人的經濟發展機會。再加上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英國人不只是希望撲滅在香港出現的民族主義意識,更想要撲滅任何同情內地社會主義的親共意識。
在整個輿論、民意主導權都落在英國人和反共人士手上的時候,愛國力量怎麼能夠成為社會的主流呢?它不斷受到主流社會和英國人的壓制,甚至有的人隨時會被英國人驅逐出境。所以不要高估當時愛國力量在香港的活動空間以及它所能發揮的政治能量。
觀察者網:您那時候有接觸過這些左派人士嗎?
劉兆佳:有。因為我父親跟內地有生意往來,他在內地購買草織工藝品,再出口到外國,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左派人士、左派團體,甚至是左派報章。
觀察者網:從個人經歷出發,您對他們有什麼印象嗎?
劉兆佳:印象不是很深刻,我自己也看過一些左派電影公司拍攝的電影,但不能說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只不過相比於一般香港人,我對他們的印象較多,也有感情存在。
觀察者網:回到之前提到的“六七事件”。“六七事件”是香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但五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很多對“六七事件”的解讀基本是從親國民黨或偏港英政府角度出發,看下來多少帶有政治上的偏見。
劉兆佳:是的。香港有部分媒體人、學者、文化人將“六七事件”看成支持中共的人為回應內地的文化大革命,違背香港主流民意的意向,在香港牽起一場反英抗暴的運動,進而導致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陷入危機。
然而,這場反英抗暴運動也帶出了香港社會內部很多矛盾,特別是勞工問題和不少底層群眾生活困難問題,也暴露了“殖民地”統治的不公平,特別是種族不公平的地方。但由於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對內地發生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害怕,當時的反英抗暴引來不少反共人士的驚恐,再加上他們不想看到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結束或受到嚴重破壞,因此不少港人就站到港英政府那邊去攻擊左派人士。
自此之後,香港的左派力量進一步邊緣化,跟主流社會的關係越來越疏離;左派代表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與主流社會的脫節程度進一步加深,彼此間的隔膜沒那麼容易消除。
這件事情不光導致左派力量在香港進一步受到孤立,甚至出現力量萎縮的情況,更麻煩的是損害了大部分香港人跟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增加了他們那種恐共、反共的情緒,所引發出來的效果甚至到今時今日都還可以感受得到。
其實如今年輕一代中根本沒什麼人留意“六七事件”,對這事也沒什麼印象。你也可以看到關於“六七事件”的比較嚴肅的學術研究基本上很少。當然,個別香港媒體對“六七事件”頗為執著,也不時通過對此事的報導提供機會讓反共人士乘機攻擊左派和中國共產黨,但總體而言影響不算大。
觀察者網:對的,內地很多讀者對香港的這段歷史也知之甚少。事件發生後,香港左派的公開活動似乎少見人提。香港左派的路線和角色做了怎樣的調整?
劉兆佳:“六七事件”之後,左派這一標籤在香港政治上已成為一個負面標籤,不過左派力量沒有從地上轉向地下,他們始終公開存在並公開活動,只是他們的政治能量、政治影響力大為減少,在香港社會上的處境越來越孤立,情況直到回歸前夕才有所改變。
“六七事件”其實也帶來一些正面效果,整件事引發不少人對香港當時社會民生及種族平等等方面問題的關注,迫使港英政府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大安主義”的管治方式——以為在管治上不需要重大改變,就可以比較安穩地進行“殖民”。
港英政府的管治變得相對開明,也更關注勞工、基層的狀況,改進了在經濟、社會、民生等方面的部分政策。當然,他們也對香港可能出現的反“殖民地”情緒與相關行動更加警惕,擔心香港再一次出現像“六七事件”這麼大規模挑戰“殖民地”管治的行動出現。
觀察者網:以往每次談及香港市民對中共的印象,不是這個負面就是那點不好,這印象多少有波動的吧?這百年來港人對中共情感如何波動起伏,能否幫梳理下?
劉兆佳:肯定有,只不過沒有人記錄得那麼清楚。譬如國共內戰期間有不少人支持共產黨,因為對國民黨實在太失望了;再比如改革開放期間,大家也對中國日後的走向有新的期盼;到今時今日,中國在經濟和科技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甚至引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擔憂,這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好感和支持。
回歸前、回歸後中央也為香港做了不少好事,當香港遇到困難的時候,中央提供協助,讓香港明顯看到中共對香港的支持及善意。回歸前最重要的是東深供水工程,以及內地在農副食品及生產原料方面對香港穩定的供應;回歸之後,幫助香港度過金融危機以及內地到香港投資、內地市場對香港開放,這些都改善了港人對中共的態度。
從中央採取“一國兩制”方針政策,讓香港在脫離英國管治之後仍可以保持繁榮穩定及原有的生活方式,到近一兩年中央撥亂反正,讓香港的社會秩序恢復穩定和“一國兩制”得以行之久遠,這些也都讓部分港人對中共產生好感。
考慮到不小比例的港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共、抗共、拒共的情緒,因此塑造好感的過程並不容易,需要以細水長流、潛移默化的方式推進。
觀察者網:之前在香港社會中,中共和中共黨員身份算是比較敏感的標籤,如果有同事或領導被懷疑是中共黨員,會引來不少輿論討論,比如據我瞭解,有位港中大前校長就曾因被懷疑為中共黨員而遭受一些反對派人士攻擊。回歸之後,香港社會對中共的認識為什麼會在較長時期內仍處於負面狀態?
劉兆佳:因為中共知道港人對共產黨一直比較敏感,甚至“中國共產黨”這五個字也是一個敏感詞語,所以中共在回歸前承諾不在香港公開活動。也因此,回歸後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基本上沒有做多少事來改變港人對中共的認識和態度,更不要說促進彼此之間的感情。一方面,這類事太敏感,容易引起政治糾紛,搞不好的話還會引發政治鬥爭;另一方面,他們覺得政治上未必有這樣的需要。
如鄧小平所說,他知道香港有不少人對共產黨有意見,所以才搞了“一國兩制”出來,讓那些所謂的反共人士可以在香港安身立命。即使你對中共有什麼意見,只要不做任何試圖推翻中共領導地位的事情,不把香港當成顛覆中共政權的基地,大家可以相安無事。
中央政府、中共不去行動,特區政府哪裡敢做?尤其是如果特區政府做的事情讓民眾覺得它是支持、認同中共的,它馬上就會面對一個難以有效管治的局面,社會上會出現很多反對它的聲音和行動。
中共、中央、特區政府都不做了,思想基地就拱手讓給了那些西方勢力及在香港存在已久的反共勢力。在政府內部也好,在教育體制、媒體也好,宗教組織也好,乃至在社會上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裡,反共勢力變成了主流力量,導致我們年輕一代受到反共思想的嚴重影響。即使在政府內部也有不少公務員和官員對共產黨有抵觸情緒,學校老師、媒體從業者及西方宗教力量更是如此,整個思想陣地都被別人佔領了。
這些反共勢力不斷利用他們在思想陣地上的主導地位,不斷利用港人反共、恐共、拒共的情緒去挑戰特區政府的管治、挑戰中央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甚至試圖將香港變成一個內外敵對勢力可以用來挑戰中共在內地領導地位的所謂顛覆基地、滲透基地。
觀察者網:您在近來的一個講座裡提到,在“一國兩制”下港人須負起維護國家安全責任,維護共產政權及內地社會主義體制的安全亦是重要。前者是必須的,對於後者,港人如何做到?如今對港人的要求應該更高吧?而不再是只需不讓香港成為顛覆政權的基地。
劉兆佳:在新時代、新形勢下,特別是香港在回歸後經歷這麼多的政治鬥爭和動亂暴亂,現在有一些問題已無可回避,因此一定要將這些問題講得清清楚楚,才有利於以後“一國兩制”的實行,才有利於香港與自己的國家、香港與內地的關係的發展。
第一,香港已回歸中國,已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也就是不能將香港看成是獨立的政治實體。
第二,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在香港也擁有全面管治權。也就是說,香港的管治不能單純由特區政府去處理,中央也有權力和責任參與管治。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全國的執政黨,只不過對於香港,是用另一種方式——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來管理,而不是由其直接治理;中國共產黨要負起香港是否能夠有效管治及是否穩定的最後責任,亦有責任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準確地實施。
第四,“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不能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不能成為顛覆基地,不能成為西方對付中國的棋子。在國家安全當中,首要的是政權安全,任何試圖改變中共領導的行動都是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
第五,你要將香港和中共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才行。因為“一國兩制”方針是中共制定出來的,而“一國兩制”既符合香港利益,又符合新中國的利益,所以如果中共的領導地位出現了問題,“一國兩制”也難以維持下去。
第六,回看過去一百年,特別是中共建國之後,中國政府一向是以支持、照顧、包容、體恤的態度對待香港的。不管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想過要做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反而不斷積極採取各種措施去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加上另外一點,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的捍衛者,在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在國家安全面臨嚴重威脅的情況之下,香港的確需要支援和配合中國共產黨在這些方面的工作,這樣才能讓“一國兩制”不會被外部勢力用來做一些不利於國家民族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要講清楚,特別是要講清中國共產黨和香港的關係。以前很多人都不敢提這個問題,導致一些人不斷挑撥離間,甚至不斷在香港製造強化反共、恐共、疑共意識,將香港和中共塑造成利益對立者。如此一來,“一國兩制”怎麼維持得下去?
觀察者網:說到公開說清關係,6月12日“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這是不是可以看作一個好的開端?即我們開始更直白、直接地向香港社會傳達有關內地政治制度、政黨制度的資訊。
劉兆佳:在香港公開討論中國共產黨和香港的關係,這是第一次,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相信中共在香港沒有明顯存在感的情況會慢慢改變。既然要改變香港人對中共的錯誤認識或反對情緒,最好是由中共自己介紹自己,不需要假手於他人。過去有關中共不在香港公開活動的承諾,今天在新形勢下已經不合時宜,更不利“一國兩制”的全面和準確實踐。
中共應該自己講解這百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共究竟對香港的發展作出過什麼貢獻;講清楚在“一國兩制”下,中國政府所做的一切怎麼符合香港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講清楚近幾年它所做的事是為了挽救“一國兩制”,將“一國兩制”的運行重新納入鄧小平所定下的正確軌道,讓“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而非放棄或扭曲“一國兩制”。
坦白說,以前有些事情想說得坦坦白白、清清楚楚,但很多時候中央會顧慮這是否會引起反對派的攻擊,或者擔心被人扭曲了本意,引起社會上的恐懼。我看今時今日,既然要撥亂反正,有些事情就要斬釘截鐵地說清楚。
反對派如今已開始潰不成軍、偃旗息鼓,其話語權已經大幅剝落,中共更要利用這個難得的有利條件,將以前很少說或者說得不夠清楚的事情坦坦白白地說出來。也就是說,在撥亂反正的重要環節奪取話語權——話語權長期以來被反對派及西方勢力所掌控,現在就是重奪話語權的時候了。
觀察者網:最後一個問題,香港目前黨派眾多,面對各個黨派——或者說不同群體——的不同政治立場和政治訴求,中央如何做黨派工作?6月25日,《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發佈,著重闡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個制度創設對於香港各黨派工作有沒有什麼借鑒?
劉兆佳:我預測過香港以後的管治形態。以前是靠特區政府單打獨鬥,但它既缺乏足夠的勇氣和對國家民族的擔當,又對西方勢力和反對勢力過度恐懼和某種程度的“認同”,表現得過度懦弱。以後有可能轉變為中央領導下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共同參與這麼一種三方合作的管治形態。內地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和協商制度放到香港,就變成中央領導下的中央、特區政府與愛國力量的合作制度。
在這個過程當中,特區政府要特別加強與愛國力量之間的協作,而特區的主要官員也要是愛國力量的中堅分子。愛國力量則需要進一步擴充,提升政治能力,包羅更多不同類型的組織和人才,讓愛國陣營在社會上能更具代表性以及有更加廣泛的社會支援。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需要更加積極運用全面管治權,以推動香港的有效管治及發展與改革工作。
加強與特區政府、愛國力量裡不同黨派團體之間的合作,這性質和精神與內地的多黨合作制多少有些相似,都講求合作、協商、共同進退、榮辱與共。